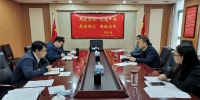人民长江报:水润我生
孙礼
与水的缘分与其说是一种偶然,不如说是一种心结。
我是水边长大的。家乡徐桥是一个繁华水镇,三面环水,一面望湖。镇的东边河,长且平阔,河水清澈,哗哗作响,是小镇的生命线,我们兄弟到河边抬水的生活,那扁担上的刻线,相互的谦让,都刻骨铭心;西边的船河,是长江的一段“盲肠”,水深且静,热闹的码头总是挤满了渔船货船,桅杆林立,吆喝四起,是小镇的商贸区,看过一次河上百舸争游的龙船赛,成我一生彩色的回忆;远眺的泊湖,天水茫茫,湖与华阳河相通,浩浩荡荡入注天堑长江,湖盛产的洁白纤细的针鱼,晒得铺天盖地,既饱口福又饱眼福;镇头的杨泗庙,是儿时玩耍的地方,大了才知道杨泗是大禹的“兄弟”,有着辅佐治水的美丽传奇。
上山下乡时,一辆独轮车把我推到了偏僻的老家高堰村。我没有感到寂寞,反而获得了亲近自然、亲近流水的时光。春水盈盈时,和村里小伙伴们光着脚丫到沟里、田里、塘里捞鱼,那是劳动和丰收最淳朴的快乐。我上学要走十几里的羊肠小路。先经巍巍高堰水库大坝,迎水平整的青色石坡,背水的槐树乌桕林,让我陶醉于亲水的多彩和壮阔。水库捕鱼竞捕到过百斤重的鱼王,让村民们欢笑;水库大水漫淹门前的农田,也让大婶们流下悲怆的眼泪。中途经过一座小桥,桥下是条宽深的土渠,春夏秋河水奔腾不息,汩汩有声,有时还能看到趴在岸边赛太阳的乌龟团鱼。最后经过的公社旁边的小小水利站,红砖青瓦的房子掩映在渠边绿色的樟树林里,路过时,常看到白鸟在树梢起舞,常闻到粗茶淡饭之香。“再苦的日子,他们都有吃的。”一句小学友稚嫩的话语却让我认定干水利是最幸福的人。
每年冬季,家里就住满了望江县来的修渠民工,大概几十人,地铺挤满了客厅客房和走廊。那时钱轻义重,完全没有报酬或嫌忌的念头。每天早晨上学,烧火的师傅就盛上一碗热热腾腾的米饭给我,周末改善伙食也总是让我全家参与;每天晚上,我就和他们挤在一个被窝里,听讲兴水治水的故事。一月两月过去,皮肤黝黑一身泥土的伯伯叔叔们修好了渠就走了。以后每当看到上学经过的土渠,就勾起我对他们的怀念,就想到水的“源远流长”。是他们,让花凉亭水库的水跨乡越县,流到遥远的家乡。
花凉亭水库是家乡安庆最大的水库,位于大别山南麓皖河支流长河的岔路乡花凉亭,具有防洪、灌溉、发电综合性功能,控制面积 1870 平方公里。花凉亭灌区远灌太湖、望江、宿松、怀宁四县100多万亩农田,然而,大坝天然的缺陷一直威胁着县城的安全,近年国家投入两个多亿除险加固,库区终于华丽转身为安徽著名的旅游区,中秋、国庆长假期间,每天有几千人来此观景游览、吟诗作画。库区养育了很多名流,安卧着赵朴初先生的佛骨,悠扬着西风洞寺庙不息的钟声。近期到合肥李氏庄园才知道,清嘉庆元年的状元赵文楷、李鸿章、赵朴初、张爱玲间的亲情和美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当年亲朋劝我:“转业请到这里来,不会亏待你。”一句话激活了我对水的梦想和期盼。每次回故乡,我都要到此深吸乡土气息,感受亲情水情。
80年代初,我到“江城湖都”武汉上军校,从安庆乘坐“东方红”江轮直达武汉的长江风光,武汉街道上挂牌水利、防汛的高耸楼群和宽敞院场,湍岸的江水直扑嘴唇的彻夜防汛,永远抹不去我依稀记得的那条水路、那条水街、那条江堤。湿漉漉的武汉把我融到了水里。
当我转业面临职业选择时,一位老革命、父辈的领导把我推荐给了水利,让我肩负泰山之重;一位老厅长“你会点儿什么”的发问,让我惶恐江河之深。十几年,我潜心烟波浩渺的湖库,逝者如斯的川水,欢歌笑语的溪流,芳草嘉树的群山,珍惜一朵小浪花的美丽,感奋滴水穿石的精神。我和水利一起成长成熟,在杂志上发表论文,畅述我所学所思,在报刊上撰写文章,畅抒我爱恨情仇。我参与了《水土保持法》以及江西地方办法的修订,留一串难忘的脚印;在讲台上向同仁讲述工作心得,留一丝飘渺余音。我有缘初识了一批老水利,感受着他们的辛劳,感动着他们的成就。如今,我又拿起笔杆,做最后的冲刺,宣传和书写炫彩的水利人生和文明、壮美的水利改革和跨越。